《南京照相馆》:一场人性炼狱里的“内在放生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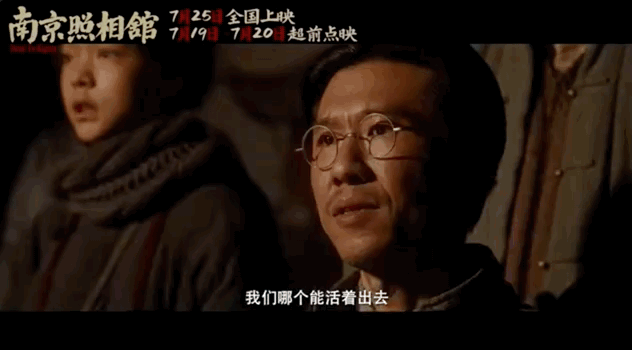
开篇 · 破框:当“我”决定逃离时,电影抓住了我
昆明的午后三点,阳光正好。我走进电影院,本是带着任务来的。
作为一个自媒体人,总想着要和世界发生点连接,蹭热点似乎是最直接的方式。本想看那部讨论度最高的片子,奈何影院没排片。时间凑巧,只剩下这部《南京照相馆》。
说实话,我内心是抗拒的。
一听这名字,就和那段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历史绑在了一起。我心里犯嘀咕:这会不会看着堵得慌?我们这一代人,生在春风里,长在阳光下,对战争、对那种极致的苦难,其实隔着一层历史的厚茧,很难有真正的体感。
我甚至都为自己预设好了“逃跑路线”,特意选了旁边没人的过道位置。
电影的前二三十分钟,似乎印证了我的预感。打打杀殺,背景铺陈,一度让我觉得,这不过又是一部消费国耻、贩卖苦难的战争片。我好几次都想站起来,顺着预设的路线,逃离这份可预见的压抑。
但,就在那“犹豫了一下子”的瞬间,一些不一样的东西,悄然发生了。
我不知道是从哪个镜头开始,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。一开始,或许只是人之常情的触动。但慢慢地,我发现自己被卷了进去,卷入的不是南京城,而是电影里每一个灵魂的内在战场。直到五点半散场,影院灯光亮起,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,不是嚎啕大哭,而是一种发自肺腑的、压抑又汹涌的悲恸。
走出影院,我一直在想,这部电影究竟做对了什么?它凭什么能击穿我厚厚的心理防线,让我这样一个自诩看过些世事、经过些修行的人,彻底“破防”?
答案渐渐清晰:它不是在讲历史,它是在讲“人”。
更准确地说,它是在我们面前,活生生地、一刀一刀地,解剖了“人性”这两个字。它呈现了一场极致环境下的“内在放生”——当所有外在的身份、道德、知识,甚至连“活下去”这个最基本的信念都被碾碎时,有什么东西,会从我们生命最深的源头,破土而出?
这,或许才是《南京照相馆》真正想让我们“照见”的东西。

第一重解码:从“活下去”到“活出人样”——小我的生存游戏与真我的觉醒
我们先来看看故事里的人。
无论是高叶饰演的、有点风尘气的女演员林毓秀,还是王传君扮演的、在夹缝中求生的翻译官王广海,亦或是刘昊然演的那个胆小善良的邮差苏柳昌,他们一开始,谁都不是英雄。
他们和我们一样,都是普通人,被卷入了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。他们最初的念头,高度一致,那就是——“活下去”。
这太真实了。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最原始的“小我”(Ego)吗?我曾听过一种说法,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是人类的天性。当危险来临,我们的大脑,那个只为“生存”而设计的机制,会立刻接管一切。它不在乎对错,不在乎尊严,它只有一个指令:活下去。
于是,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无比熟悉的人间游戏。每个人都在玩着自己的“心理游戏”,遵循着各自的“人生脚本”。林毓秀的脚本是“依附强者”,她认为靠着她的男人王广海,就能得到庇护;王广海的脚本是“妥协求存”,他告诉自己“我只是个翻译”,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;苏柳昌的脚本是“逃离危险”,他只想尽快离开这座人间地狱。
在和平年代,我们的脚本可能是“要成功”、“要赚钱”、“要被爱”。而在1937年的南京,所有人的脚本都被简化成了最赤裸裸的一句:“我要活”。
然而,真正的修行,恰恰是从这套“大脑”的逻辑系统失灵的那一刻开始的。
转折点是什么?是“看见”。
是那个叫宋存义的士兵,在烧水时,猛然从一堆照片中,看到了自己亲弟弟被刺刀贯穿的影像。那一刻,他崩溃了。我在播客里也分享过,我也有姐姐,看到那一幕,我的眼泪“哗”地就下来了,完全绷不住。因为在那一刻,所有的“生存逻辑”都失效了。那不是一个“待处理的尸体”,不是一个“战争中的牺牲品”,那是“我弟弟”——一个与你生命最深处紧密相连的存在。
是那个被日军军官嫌吵,而被活活摔死的婴儿。那一刻,照相馆里所有人都被震碎了。我当时在影院里,感觉一股血直冲头顶,真的想冲进屏幕里杀了那个畜生。为什么?因为那个场景,击穿了我们大脑里所有关于“合理化”的防御机制。你可以为杀戮找到一万个理由——战争、命令、立场……但你无法为一个婴儿的惨死找到任何理由。那一刻,暴露出来的是纯粹的、不容置辩的恶。
也正是从“看见”这些无法被“大脑”所解释、所容忍的真相开始,这些角色的“心”,开始醒了。
他们发现,“活下去”这个脚本,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活下去的代价,是看着亲人被虐杀而无动于衷,是看着婴儿被摔死而保持沉默,那样的“活”,还算“人”吗?
从那一刻起,一场内在的革命开始了。他们不再仅仅是求生的动物,他们开始想要“活出人样”。那个沉睡的“真我”,那个超越了生存算计的、与所有生命休戚与共的本源,开始苏醒。高叶饰演的林毓秀,从一个只想依附男人的戏子,喊出了“我们有未来吗?”。她唱的不再是靡靡之音,而是穆桂英、梁红玉,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节。刘昊然饰演的苏柳昌,把逃生的机会一次次让给别人,喊出了“我们中国人不许可你们这么糟蹋”。
这,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“内在放生”。他们在放生的,不是别的,正是那个被恐惧和生存逻辑捆绑了几十年的“小我”。他们选择走向死亡,恰恰是为了完成一次作为“人”的真正诞生。这正如《悉达多》中的主角,必须抛弃所有身份,历经所有苦难,才能最终在河边找到真我。这些角色,也在南京这条血河边,找到了他们自己。

第二重解码:“仁义礼智信”的屠刀——当“知识”成为“大脑”的骗局
这部电影最让我不寒而栗的,不是血腥的场面,而是那个日本摄影师伊藤,以及他那位满口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上司。
伊藤这个角色,塑造得太成功了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脸谱化的恶魔,恰恰相反,他文质彬彬,爱好摄影和电影,甚至在开头还流露出一种“善良”和“恻隐之心”。
这太具有迷惑性了。在很多以往的电影里,这种角色往往会被塑造成“良知未泯的侵略者”,用来探讨所谓的“人性复杂”。但《南京照相馆》狠狠地撕下了这层虚伪的面纱。
伊藤的“善”,是一种不动脑筋的、自动化的表演,是大脑精心计算后的结果。他救苏柳昌,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工具人;他喂狗,是为了彰显自己的“高贵”;他对苏柳昌说“朋友”,是因为他把他当成可以驯服的宠物。
他的上司更是将这种“大脑的骗局”演绎到了极致。他用毛笔写下“仁义礼智信”,然后用这五个字,去解释他们所有的暴行:不杀你们是“仁义”,给你们通行证是“信用”,借刀杀人是“智慧”。
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文章里,在课堂上反复说的,“知识”与“真知”的区别吗?
这些日本人,他们拥有“知识”。他们读中国的典籍,了解中国的文化,但这些“知识”对他们而言,只是工具,是用来包装和合理化自己兽行的华丽外衣。这些知识进入了他们的大脑,却从未触及他们的心。
我想起《道德经》里的一句话: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”意思是,追求知识的人,每天都在增加;而追求“道”的人,每天都在减少。伊藤和他的上司,就是“为学日益”的极端。他们的行为,不是发自于对生命当下的感受和尊重,而是被一套名为“军国主义”、“家族荣耀”的、来自过去的、僵死的“知识系统”所驱动。
所以,他们可以一边引用着“仁义”,一边策划着屠杀;可以一边谈论着艺术,一边对镜头里的惨状无动于衷。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,中国人不是和他们一样活生生的人,而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“概念”,一个可以被他们的“知识”所定义和解释的“他者”。
这才是最深层的恐怖。它告诉我们,最大的恶,往往不是源于无知,而是源于被扭曲的“知识”。当一个人完全被他大脑里的那套逻辑系统所操控,失去了与“心”的连接,他就可以做出任何反人性的事情,并且心安理得。这正是我在《致被大脑所骗的灵修者们》一文中所担忧的,当大脑的逻辑系统掩盖了本源的我们,“真我”与“自我”的博弈便开始了。
电影用一勺腐蚀性极强的显影液,泼在了伊藤那张“文明”的脸上,让他瞬间“显影”出了恶鬼的原型。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——真相,有时候需要用最激烈的方式,才能被揭示。而我们每个人的修行,不也正是在用“觉知”的显影液,去冲洗自己大脑中那些虚伪的、自欺欺人的“知识”底片吗?

第三重解码:一张照片的重量——“看见”是痛苦的开始,也是解脱的唯一法门
整部电影的题眼,是“照相馆”,是那一卷卷底片,一张张照片。
照片是什么?是真相的切片,是时间的琥珀。它有一种不容置辩的力量,强迫你去“看见”。
在那个黑暗的年代,语言是苍白的,道理是可以被歪曲的,但一张照片,一个被定格的瞬间,却能以最沉默、也最雷霆万钧的方式,告诉你何为真实。
照相馆的老板金承宗、邮差苏柳昌、女演员林毓秀……他们之所以能完成从“小我”到“真我”的蜕变,起点都是因为他们“看见”了那些照片。他们看见了昔日笑容满面的邻里,变成了照片里冰冷的、被砍下的头颅;他们看见了熟悉的街道,变成了尸横遍野的修罗场。
这种“看见”,是痛苦的。它像一把尖刀,刺破了所有人“只要我假装看不见,灾难就与我无关”的幻想。它强迫你承认,你和那些受难者,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。他们的痛苦,就是你的痛苦。
但这种“看见”,也恰恰是解脱的唯一法门。
在修行的路上,我们常常谈“觉知”、“观照”。是什么意思?就是如实地“看见”,不带评判、不加扭曲地看见自己内在的起心动念,看见那些我们一直试图逃避的恐惧、愤怒和悲伤。
电影里的暗房,就是一个修行的隐喻。在那个伸手不见五-指的红色暗室里,真相在药水中一点点浮现。这个过程,不正像我们在静心中,潜入自己意识的暗房,看着那些被压抑的念头和情绪,在觉知的“显影液”中,慢慢显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吗?
一开始,这个过程是痛苦的,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你不想承认的“丑陋”。但只有当你敢于直面它们,你才能从中解脱。电影里的角色们,正是在直面了那些照片里的地狱真相后,才从“活下去”的恐惧中解脱出来,获得了“为某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而死”的巨大勇气。
他们拼死要送出去的,已经不仅仅是几卷胶片,而是“看见”这个行为本身。他们要让全世界都“看见”,要让历史“看见”。因为他们明白,遗忘和否认,是对死者最残忍的二次屠杀。而“看见”,是治愈的开始,也是正义的起点。
当高叶饰演的林毓秀,在影片的最后,举起相机,拍下战犯被枪决的瞬间,快门声与枪声重叠。那一刻,相机不再是记录美的工具,它成了一把审判的武器。它告诉我们,“看见”本身,就是一种力量。
如果你也曾被某个瞬间的“看见”所震撼,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,还是一部电影带来的冲击,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

结尾 · 点睛升华:那束在暗房里冲洗出的微光
走出电影院,昆明的傍晚,天色渐沉。我没有像看完很多电影那样,急着去刷影评,去跟人讨论。我只想静静地走一会儿。
我在想,这部电影最终留给我们的,是什么?
是仇恨吗?当然有。看到同胞被那样凌辱,那种发自肺腑的愤怒,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情感。但我知道,导演想表达的,远不止于此。
如果仅仅是宣泄仇恨,这部电影的格局就小了。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“压力测试”。它把所有的角色,乃至屏幕前的我们,都扔进了一个巨大的“炼丹炉”,用战争、死亡、绝望的烈火反复煅烧,最终想看看,能炼出什么“真金”来。
电影给出的答案是:人性中那点不死的微光。

那是在最深的黑暗中,依然选择善良的微光;是在必死的绝境里,依然选择牺牲的微光;是在“小我”的废墟上,升起的“真我”的微光。
这让我想起了《了凡四训》里说的“命由我作,福自己求”。在那样一个命如草芥的年代,这些普通人,用他们最后的行动,夺回了自己生命的主动权。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,但他们决定了自己要“如何”去死。他们用自己的“作”,为这个民族求来了一线生机的“福”。
所以,我为什么会推荐这部电影?
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,虽然没有战争的硝烟,但我们每个人,不也正处在各自的“南京城”里吗?我们被焦虑、被内卷、被各种无形的压力围困,我们的大脑不也天天在用各种“生存逻辑”告诉我们要妥协、要苟且、要“活下去”就好吗?
我们是否也常常因为害怕“看见”真相而选择麻木?我们是否也被各种看似正确的“知识”所绑架,而忘记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?
《南京照相馆》就像一声棒喝。它提醒我们,在任何时代,真正的敌人,从来都不是外在的困境,而是我们内在那个选择妥协和麻木的“小我”。而真正的救赎,也只能来自于我们内在“真我”的觉醒。我曾在一本书里读到,真正的宝藏不在金字塔下,而在出发的地方,在自己的心里。
影片的最后,当那些遇难者的黑白照片,与今日南京城的繁华景象交叠在一起时,我再次泪崩。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,正是由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,用生命守护那点“人性微光”换来的。
这部电影最终留下的,不是仇恨,而是一面镜子。它照见的,不是南京的废墟,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,那个在苟且与觉醒之间挣扎的灵魂。而那束在暗房里冲洗出的微光,不仅是历史的真相,更是我们每个人生而为人,必须守护的人性之光。
最近,我开始尝试用我独特的视角,去“照见”更多电影背后的深意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“借影修心”的方式,请一定在评论区告诉我,你们的每一个留言,都是点亮我前行的光。也欢迎大家点赞和转发,让这束微光,被更多人看见。
【联系我】
